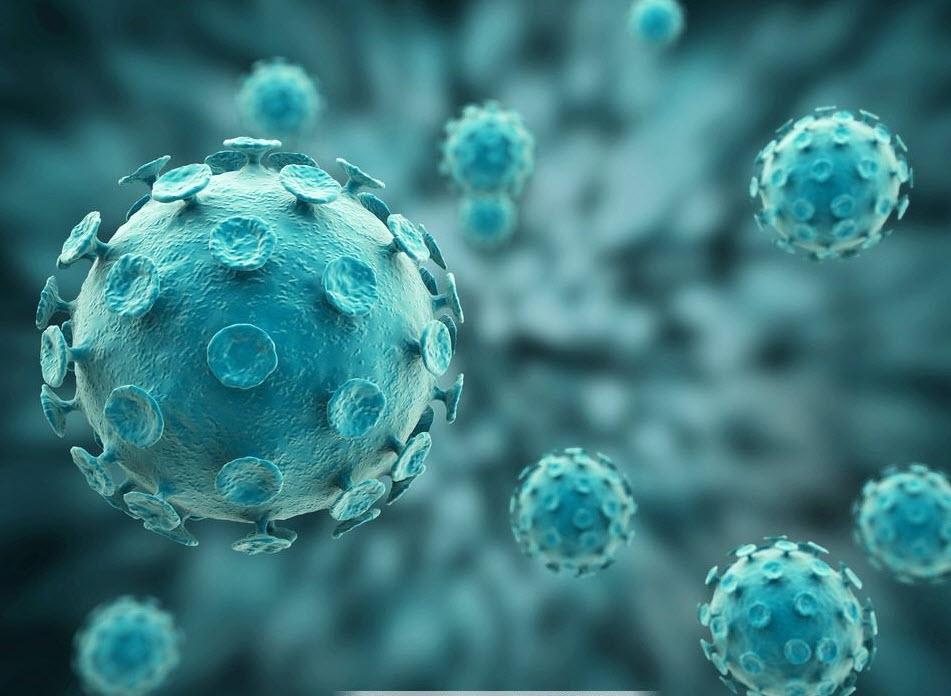
2019年春季和夏季,“僵尸鹿病毒正在北美蔓延”的新闻不断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难道僵尸这东西真有其事?这种“僵尸鹿病毒”会不会传染给人类,把我们也变成僵尸?面对这些疑问,病毒倘若有知,怕是要哭晕在厕所了,因为它们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导致“僵尸鹿”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朊病毒”。名字中虽有“病毒”二字,但它根本就不是一种病毒,而是一类有点特别的蛋白质。虽然不是病毒,但朊病毒的可怕之处却丝毫不逊于病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的疯牛病就是朊病毒引起的,而我们的多种神经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都与朊病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朊病毒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这一切要从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深处的食人族说起。
新几内亚岛位于澳洲大陆以北,紧靠赤道南侧,面积比我国青海省略大。这个仅次于格陵兰岛的世界第二大岛上人烟稀少,很多地方保留着原始状态,比亚马逊雨林还要神秘。
新几内亚高地由西向东横贯整个新几内亚岛,特别是在岛东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境内,高地占据了陆地面积的大部分。来自亚洲的人类祖先在大约3万年前登上这座海岛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这些山地雨林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197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上迎来了一位美国神经学家,名叫斯坦利·布鲁辛纳(Stanley Prusiner)。虽然这里的原住民始终保持着近乎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对于这帮摆弄各种古怪仪器的科学家们却并不陌生。这里的孩子们甚至会组成小队,专门帮科学家跑腿,并以此为乐。但是,雨林的孩子们却并不太喜欢布鲁辛纳。这位科学家虽说不算太胖,但明显是个缺乏锻炼的人。在沿途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孩子们不得不推着布鲁辛纳往上爬,累得筋疲力尽。
好不容易到达当地部落之后,布鲁辛纳没住几天就又闹起了肚子,情况还很严重。这回倒霉的就是部落里的成年人了,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布鲁辛纳运下了山。尽管这趟短暂的实地考察与想象中轻松愉悦的热带旅行相去甚远,但布鲁辛纳却觉得不虚此行,因为他终于有机会亲自探访了库鲁病人。
库鲁病是一种仅仅会出现在新几内亚高地上的怪病,甚至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最罕见的疾病。“库鲁”这个词在当地人的语言中是“打冷战”的意思,因为这种病人会出现不自觉的抽搐现象。此外,他们走路跌跌撞撞,时常昏睡,伴有头痛。最可怕的是,库鲁病人到了晚期就开始狂笑不止,毫无理由,自己也停不下来。他们甚至会笑得倒在地上打滚,哪怕从一堆篝火上滚过去也浑然不知,更不会停止发笑。狂笑之后便是死亡——这是库鲁病人唯一的归宿。因此这种病也被称为笑病。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地的成年男性从不会得这种病,只有成年女性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们会得这种病。这种性别差异性更加重了库鲁病的神秘性,也无怪乎当地人认为这是妖魔鬼怪带来的疾病,唯有通过巫术才能解决。
科学当然不是巫术。但在新几内亚高地土著人的眼中看来,科学与巫术无异,甚至还不如巫术,因为科学家们也治不好他们的库鲁病。
布鲁辛纳既不是第一个来到新几内亚高地研究库鲁病的科学家,也不是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早在布鲁辛纳登岛的21年前,一位同样来自美国的科学家丹尼尔·卡尔顿·盖杜谢克(Daniel Carleton Gajdusek)来到了这座远离尘世的雨林中研究库鲁病。
别的科学家来到新几内亚高地都是被库鲁病所吸引,却像布鲁辛纳一样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盖杜谢克来到这里却如同鱼入大海一样自由自在。他不仅着迷于库鲁病本身,也着迷于这里的土著文化以及雨林中的生活方式。他与帮助他的土著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甚至后来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接到了美国读书。
然而,盖杜谢克并没有成为一位遁世的隐士,他仍然与现代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时已经有科学家通过尸体解剖发现库鲁病人的脑中会出现奇怪的蛋白斑块,还有神经元的大量死亡,把脑组织搞得像海绵一样有很多孔洞。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小脑区域,故而影响了病人的运动能力。但是对于致病原因,很多科学家归咎为遗传病。盖杜谢克却不认同这一点,他发现库鲁病虽然会出现在同一家人中间,但也的确会出现在病人家庭之外没有血亲的族人身上,说明它更像是一种传染病。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盖杜谢克在美国的一处乡村地区建立了一个灵长动物实验室,把死于库鲁病的病人脑组织注射到了两只黑猩猩的脑中。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两只黑猩猩一切正常,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时,盖杜谢克以及整个科学界都不可能意识到,时间才是关键因素。三年后的1966年,两只接受了病人脑组织注射的黑猩猩相继出现了类似库鲁病早期的状态,步态断断续续,跌跌撞撞,无法正常走路。然而身体检查表明,它们在各方面都仍然是“健康”的状态。
盖杜谢克闻讯从新几内亚雨林赶回了美国,亲自检查之后决定对两只黑猩猩实施安乐死,然后进行脑组织检查。结果,它们的脑中果然有像库鲁病一样的斑块和海绵状孔洞。结论已经很明显了:有某种病原体在脑中滋生导致了库鲁病,并且可以传染给其他人,甚至是其他灵长类动物。
盖杜谢克的团队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一篇论文,两周后被《自然》发表。由于脑组织中并没有观察到任何形态的细菌或真菌,于是他们推测这种病原体是一种未知的新病毒,并给它命名为“慢病毒”(slow virus,并非今天“慢病毒”一词所对应的lentivirus)。
虽然库鲁病的原凶似乎找到了,但是它的传播途径依然是个迷。如果它真的像其他病毒那样传染的话,为什么来此地考察的科学家们无一感染这种疾病呢?
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库鲁病几乎只出现在法雷人(Fore)这个部族当中,而这个部族有一个其他部族都没有的生活习惯——食人。当然,这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吃掉敌方俘虏的血腥场面,而是将自家已故亲人的遗体吃掉,把悲伤的葬礼变成一场饕餮盛宴。
虽然这种习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相悖,但也的确有其科学解释。要知道,在新几内亚岛这样一个地理隔绝的环境中,一旦原生的大型动物被人类祖先屠戮殆尽,当地人就会面临严重缺乏蛋白质来源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把死去亲人的身体吃掉,也算是一种“肥水不流外人田”,能够有助于提高部族的营养水平和战斗力。
经过长年观察,有科学家提出,库鲁病的传播很可能与法雷人的食人习俗有关。但是,仍有两件事情解释不通。第一,法雷人的食人习俗规定,只有妇女才有权利吃掉死者的脑,为什么孩子们也会被传染?第二,在西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法雷人的食人习俗在1950年代就已经彻底废除了,为什么库鲁病人仍不断出现?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发现与母爱有关。原来妈妈们都觉得肥腻的脑白质和灰质是不可多得的美食(我国部分地区的人民一定也会赞同这种美食观),于是总会偷偷违反习俗规定,分一些死去亲属的脑给孩子们吃。而第二个问题则在盖杜谢克的黑猩猩实验中得到了解答,库鲁病的病原体即便是直接注射进脑中也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发病,那么通过饮食摄入的话,可能会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到了1960年代末期,在远离食人习俗十余年的法雷人当中,库鲁病已经变得相当罕见了。到了1970年代末期,巴布亚新几内亚摆脱了澳大利亚的殖民统治之后,库鲁病再也没有出现在这座高地上。
1976年,盖杜谢克因为他在库鲁病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关于诺贝尔奖有句笑谈:如果想得诺贝尔奖,你首先得保持健康,活得足够长久。这是因为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发错奖的问题,于是评奖委员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往往要等一项发现已经被科学界反复确证之后才敢颁奖。
在库鲁病的问题上,盖杜谢克的获奖无疑是实至名归的。但是“慢病毒”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是病毒感染,为什么库鲁病人的脑组织没有出现任何炎症反应?为什么就连动用了电子显微镜也观察不到这种病毒的身影呢?为什么高温、脱水、紫外线照射,甚至是核辐射这些消毒手段都无法杀灭这种病毒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不禁令科学家们怀疑:导致库鲁病的原凶真的是一种病毒吗?
从新几内亚高地归来的布鲁辛纳,显然不会像盖杜谢克那样与那片雨林建立情感的联结。但是或许距离才能令人更加清醒地保持客观的视角。布鲁辛纳回到美国之后提出,导致库鲁病的原凶不是真菌或细菌这样的生命体,也不是病毒这种界定上存在争议的生命体,而是一种生命物质分子——蛋白质。
细胞内部充满了蛋白质组成的“建筑”与“机器”(图片来源:The Inner Life of a cell)
大多数人对于蛋白质的认识都停留在营养品这个水平上,只知道肉、蛋、奶、豆中富含这种物质。而谈及生命科学,人们大多会想到基因。可实际上,基因不过是细胞生产蛋白质时所参照的编码而已,蛋白质才是构成生命体的一砖一瓦,是驱动生命运转的机器零件,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蛋白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就是它的功能与其三维结构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化学上讲,大多数蛋白质都是一条一维的长链,更准确地说,是一条由氨基酸按基因编码排列而成的序列。但是,这条一维的长链并不能发挥蛋白质的功能。它要像小朋友玩的魔蛇一样,通过扭转折叠,形成三维的立体形状,才会具有功能。
蛋白质分子不会直接引发炎症反应,尺寸也太小,无法在盖杜谢克那个时代的电子显微镜下直接观察到。另外,蛋白质分子的化学稳定性不错,不会在高温、脱水、紫外线照射或低剂量的核辐射下被破坏。因此,布鲁辛纳确信:根本没有什么“慢病毒”,真正引发库鲁病的应该是一种蛋白质分子。
很显然,布鲁辛纳是个颇为自信的人,也很喜欢出风头。他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已经给自己的新发现取了个名字,叫做prion。这个词是蛋白质protein的前三个字母和感染infection的前两个字母拼合而成。可他又觉得proin不好读,不像一个英语单词,于是改成了prion。布鲁辛纳曾经亲口承认,自己觉得这个词很“时髦”。
不过大多数科学家对于时不时髦这种事情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们更在乎的是证据。由于布鲁辛纳给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prion这个概念受到了科学界普遍的抵制,其中就包括库鲁病领域的绝对权威盖杜谢克。有一次布鲁辛纳出于礼貌,把盖杜谢克加到了自己一篇论文的作者之中,结果就被盖杜谢克给“绑架”了。直到布鲁辛纳同意删掉论文中所有prion这个词之后,盖杜谢克才签字同意发表这篇论文。
顶着几乎是整个学界的反对声音前行,布鲁辛纳对于prion的研究之旅恐怕比他当初爬上新几内亚高地还要困难百倍。然而他从未放弃,并在1982年成功分离出了导致库鲁病的prion蛋白分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成功的喜悦极其短暂。布鲁辛纳想要知道这种致病性的prion蛋白来自何种生物,结果却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脑细胞中都会生产这种prion蛋白。难道说,我们每个健康人的头脑之中,也都存在着能够导致库鲁病的罪魁祸首吗?会不会是布鲁辛纳在分离prion蛋白的过程中搞错了呢?
很快,布鲁辛纳自己找到了答案。问题就出在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上。
通常,当生物学家们在谈论一个蛋白质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这个蛋白质的一维长链序列。也就是说,基因编码所决定的氨基酸排列顺序就“代表”了一个蛋白质。这种代表与对应关系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只要序列确定,那么这条氨基酸的长链就一定会折叠成它自己特定的三维结构。
然而,生物学最“讨厌”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有例外。相当一部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可变的,经典情况是有两种结构状态,可以通过消耗能量在两种状态之间变来变去。这也正是此类蛋白质行使功能的方式。应该说,蛋白质形成的三维结构不像是硬梆梆的砖头,而更像是一个柔软的线团,还是能够变形的线团。
导致库鲁病的prion蛋白就是这种具有两种结构状态的蛋白质,只不过这两种结构并不全都是天然的正常状态。其中有一种结构状态是天然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好”的结构状态;另一种则会导致库鲁病,我们姑且称之为“坏”的结构状态。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prion从好的状态变成了坏的状态呢?答案出乎所有科学家的预料,竟然就是坏的prion自身。也就是说,本来一个健康人脑中的prion蛋白都处在好的结构状态。如果有一个坏结构状态的prion来到这个脑中,就会拉着身边的prion从好变坏,完全就是分子水平上的“近墨者黑”。这有点像是一种“传染”,坏的prion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那些在病人脑部观察到的蛋白斑块。这也是为什么发病需要很长时间的原因,因为这个指数发展曲线的初期是极其缓慢的。
在前文中,笔者始终使用了prion这个英语单词,却没有使用它的中文译名——朊病毒。原因恐怕很多读者已经想到了:prion根本不是病毒。不过,要洗清病毒的“冤屈”,恐怕得先从另一个不太贴切的翻译说起,那就是“蛋白质”。
前文简单介绍了蛋白质的功能和重要意义,以及很多人对它的误解。这种误解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蛋白质”这个糟糕的译名。的确,蛋白质最早是从鸡蛋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译名体现了它的制备来源,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它的本质来。
英语中的蛋白质这个词protein,是由瑞典化学家永斯·贝采利乌斯(Jöns Berzelius)于1838年命名的,源自希腊语单词proteios,意为“首要的、原初的”。这个词根充分体现了蛋白质分子对于生命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倘若按照这个思路,protein应该译作“原质”或“元质”更为贴切。
在日语中,protein也是译作“蛋白质”的,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汉字。有学者认为,“蛋白质”如同清朝末年的很多其他科技词汇一样,是由日语的翻译直接拿来的。然而也有学者提出,这些科技词汇中的大部分是由清廷设立的同文馆先行翻译,后又流入日本,并被日语直接采用的,“蛋白质”也在其列。无论源出何处,错已铸成。似乎无论科学界还是科普界都没有对待“进化论”与“演化论”那样的热情去讨论“蛋白质”的问题。
其实在蛋白质的翻译问题上,一直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就提出可用“朊”这个字来表示蛋白质。虽然这与“朊”的本义相去甚远(一说胃脯,一说人的阴部),但从构字的角度来说,肉月旁代表了生物,元代表了“首要、原初”之义,也不失贴切。只是这种提议一直都不被主流所采纳。
终于,在prion的翻译上,“朊”字被“扶正”了,用朊病毒来表示“蛋白质的病毒”。只可惜,修了东墙又倒了西墙——因为prion压根就不是一种病毒,而是一种蛋白质。它既没有病毒颗粒的衣壳,也没有衣壳里的DNA或RNA这些遗传物质。所以prion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传染性蛋白质”,或者搞得“时髦”一点就是“朊毒”。
其实,prion中文译名的不妥,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个翻译问题,而是体现了我们对于prion的认知匮乏,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迷。虽然我们已经知道prion蛋白导致了库鲁病,但是其中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究竟是“好”prion的缺失导致了神经元的坏死,还是“坏”prion聚集成块,“挤”死了神经元?我们仍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关于prion和库鲁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个病人脑中那第一个处在“坏”结构状态的prion又是怎么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针对克-雅氏病的研究或许能给出答案。
1920年代,两位德国医生最早记录了这种病症,克-雅氏病因此得名。它的早期症状是记忆力衰退和运动能力失调、肌肉痉挛,晚期则是迅速发展的痴呆、幻觉、失语、平衡力丧失、运动障碍,直至死亡。这些发病过程与库鲁病非常相似。实际上,早在1957年就有科学家发现,克-雅氏病的死者脑组织中有着与库鲁病一样的海绵状孔洞以及蛋白斑块。那一年,盖杜谢克才刚刚来到新几内亚高地。
克-雅氏病的致病原因同样是个迷。相当多的病例是毫无规律,零散发生的。后来又发现该病在一部分病人的家庭中有着遗传性。到了1970年代,接连有病例报道是由于使用了其他克-雅氏病人在诊疗过程中使用过的医用器械而导致的传染,比如经过了彻底消毒的银质脑探针电极。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令病因更加扑朔迷离。
然而,布鲁辛纳的prion给出了终极答案:克-雅氏病也是由引发库鲁病的同一个prion蛋白所引发的,但是处于“坏”结构状态的致病prion蛋白来源却可以多种多样。有可能是病人身上编码prion蛋白的基因恰巧出现了某个突变,而这个突变会导致prion上某一位的氨基酸变换了种类,于是影响了三维结构,使得它更倾向于折叠成“坏”的状态。这种由基因突变引发的克-雅氏病就会表现出家族遗传性来。
坏的prion蛋白也可能是由其他克-雅氏病人的脑子中传染而来的,途径就是像脑探针电极这种会刺入脑内部的医用器械。但是,这些器械在上一位病人脑中使用之后都是经过了严格消毒的。虽说这些消毒手段不能在化学上破坏蛋白质,但足以破坏蛋白质脆弱的三维结构。事实上,法雷人吃的也不是“人脑刺身”,而是蒸煮过的人脑,为什么竟不能破坏prion的坏结构状态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等到了新世纪。通过专门研究蛋白质三维结构的结构生物学手段,科学家们发现所谓“坏”的结构状态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拉锁的层叠结构。一条拉锁很好破坏,但是当很多prion蛋白形成一根又一根的“拉锁”,紧密地并拢成一大捆的时候,想要破坏它就很难了。这样的结构完全有可能不会被高温或脱水所彻底拆毁。要知道,哪怕只剩下一个坏结构状态的prion,它都足以在人脑中兴风作浪了。
然而,单是基因突变和医用器械感染,还不足以解释所有克-雅氏病人的病因。受到食人族法雷人的库鲁病启发,科学家们意识到克-雅氏病很可能也有通过食物传染的途径。这一猜测最终在1990年代得到了事实的残酷证明。
1980年代末期,英国的养牛场里开始出现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的牛会变得跌跌撞撞,疯疯癫癫,由此命名为疯牛病。对病牛的解剖发现,它们的脑中出现了像克-雅氏病和库鲁病一样的海绵状孔洞,以及蛋白斑块。因此,这种病的正式名称被称为牛海绵状脑病。
很快,疯牛病呈现了疯狂传染的爆发态势,几年间就出现了数万个病例。可是还没等人们研究清楚疯牛病的来龙去脉,1990年代初期,英国又开始出现多例人类克-雅氏病患者,并有患者相继死去。很快,人们就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1996年,英国官方宣布了疯牛病的存在,对于病牛的大规模宰杀和深埋也就此展开。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有多少病牛此前已经进入了流通渠道,于是人人自危的大恐慌在英国蔓延开来。隔岸观火的欧洲大陆地区也未能独善其身。疯牛病后来甚至还出现在了北美和日本。
科学研究已经证实,疯牛病也是由布鲁辛纳所发现的prion蛋白引起的。如果人食用了病牛的牛肉,就有一定机率患上克-雅氏病。如果牛肉没有经过高温烹制,那么患病的机率就会更高。英国官宣疯牛病之后的次年,布鲁辛纳因其对prion蛋白的发现和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而此时库鲁病已然绝迹二十余年。
同样由prion引起,人的克-雅氏病没有高传染性,而疯牛病却扩散得很快,这与欧美养牛场的喂养方式有关。他们会把牛身上卖不掉的部分制成肉骨粉添加到牛饲料中,用以提高牛的蛋白质摄入量,进而提高产肉量和产奶量。这些卖不掉的部分当然包括脑组织,也就为prion蛋白的传染大开方便之门。
在prion的问题上,牛和黑猩猩和人并不是多么特别的物种。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像这样自己变成了一种“坏”的结构状态,还能把身边“好”的结构状态也带成“坏”的结构状态的prion蛋白,其实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甚至在昆虫、细菌的细胞内也有发现。
当然,我们关心的往往是一些更为宏观的大型动物。比如羊也会患上prion引起的海绵状脑病,俗称羊痒症。病羊除了运动能力失调,还会不停地找地方蹭痒,因而得名。事实上,羊痒症的研究还对库鲁病的研究有过一定的帮助。早在1959年,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库鲁病人的脑组织与羊痒症的病羊脑组织非常类似,都有着海绵状的孔洞,从而建立了两种病之间的联系。
另一种能够患上海绵状脑病的大型动物就是鹿。由于它们患病后不协调的步态就像是僵尸一样,因此得名僵尸鹿病,也就是今年几次出现在新闻中的主角。当然,这种僵尸鹿病并不会传染给人类——只要你不吃它们就好。
只要你不吃它们就好——这似乎很容易就能做到,但对某些食客来说,却绝非易事。
俗话说:病从口入。要想避免患上无法逆转也无法治愈的克-雅氏病,就要“管住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吃各种“野味”!很多人(既包括喜食野味的人,也包括不吃野味的人)都认为野生动物有着特殊的营养价值,但就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明确例证。然而,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却是明明白白的。要知道,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远远多于在检疫制度下严格管控的家畜。比如2003年在我国肆虐的SARS病毒,很可能就是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再传播给人类的。
疯牛病在英国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食用带有坏prion蛋白的病牛可以引发人的prion蛋白变坏,从而患病。那么食用的野生动物如果恰巧也带有坏的prion蛋白,肯定也会让人患上克-雅氏病。事实上,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推测的“可能性”,而是十分确凿的病因。在美国纽约就曾经出现了因食用中央公园里的野生松鼠而患上克-雅氏病的案例。
其实,prion相关的疾病还不只是库鲁病和克-雅氏病而已。比如一种大量存在于神经元中的Tau蛋白,对于神经元长长的轴突有着非常重要的维护作用。科学家发现它也有类似于prion的特性,具有一好一坏两种结构状态,其中坏的状态有一定的“传染性”。而Tau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有可能是致病的罪魁祸首之一。
人脑的prion蛋白本身也与阿尔茨海默病脱不开干系。在科学家们提出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另一种病因假说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一种能够形成淀粉样沉淀的蛋白,而这种蛋白在健康人的脑中正是与prion蛋白相结合的。只不过,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认识仍然很匮乏,尚不知道这些蛋白质发生的变化究竟是因还是果。
无论确切的病因如何,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成果表明,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这两种发生在脑中的神经系统疾病,还与我们的肠道有着密切的关系。知名学术期刊《神经元》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称,α-突触核蛋白能够从小鼠的肠道组织中,经由迷走神经这条高速公路直达脑部的神经元。这种α-突触核蛋白正是在帕金森病人脑部常见的异常蛋白斑块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恰恰也是一种prion蛋白,有一好一坏两种状态,其中坏的状态有一定的“传染性”。
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最终被更多独立研究所证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帕金森病这种影响病人运动功能的脑神经疾病,很可能也是“病从口入”的。而且,这种从口而入的“病原体”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真菌、细菌或病毒,而是远远比它们都要简单得多,却也更难破坏、更难消灭的prion蛋白质分子。无论怎么看,这类具有“传染性”的“坏”蛋白质,似乎只是大自然一个精巧的错误而已。无奈的是,我们对于这种精巧的造物还所知甚少,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