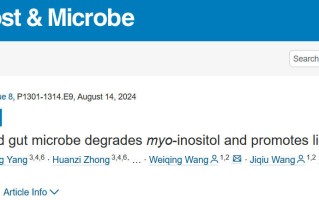《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1],比利时鲁汶大学的Jeroen Raes教授带领团队发表研究,他们完成了首个探究肠道微生物和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人群水平研究,确定了与抑郁症相关的特定肠道微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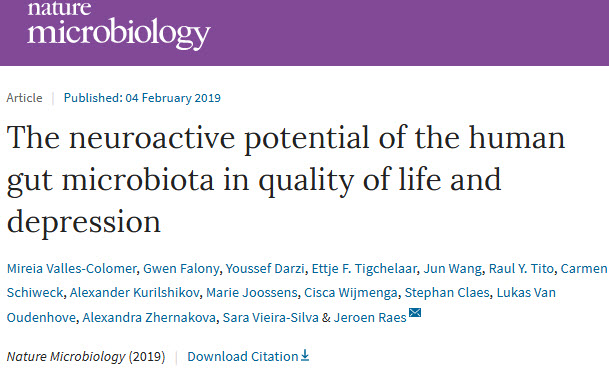
现代人,经济水平上去了,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就高起来了,基于近年来肠-脑轴的研究,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肠道微生物与心理健康之间也存在联系,但是研究多是在动物模型中进行的。为了让这种联系更有说服力,Raes教授“就地取材”,利用他们创建的比利时弗兰德肠道菌群项目(Belgian Flemish Gut Flora Project,FGFP)开展了研究。
研究人员使用RAND-36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调查问卷对队列中志愿者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进行了统计。这份调查表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活质量调查问卷,它包含4个心理方面和4个生理方面的内容,分数越高,表明健康状况越好。对于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来说,无论是否进行抗抑郁治疗,RAND-36的评分都会明显低于健康人。
研究人员还收集了队列中志愿者的粪便样本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组成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联系,并且筛选出了具有相关性的10个属的细菌。研究人员用另一个来自荷兰的队列对这个结果进行了验证,两个队列共同证明,高丰度的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和粪球菌属(Coprococcus)细菌与高的生活质量有关,反之,高丰度的黄杆菌属(Flavonifractor)与低的生活质量有关。
粪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细菌都是丁酸盐产生菌,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增强肠道屏障的功能,以前的研究也发现,这两个属的细菌在炎症性肠病和抑郁症患者中都会明显减少[2,3]。
要说心理健康呢,抑郁症是一定会被cue到的,毕竟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心理障碍。这一点在FGFP队列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队列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志愿者比例达到了11.5%。与前面的生活质量相似,研究人员也发现了4个属的细菌与抑郁症存在联系。不过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丰度。因此,研究人员排除了药物影响,大浪淘沙后发现,无论是否使用抗抑郁药物,小杆菌属(Dialister)和粪球菌属细菌在抑郁症患者都会呈现明显减少的趋势,这个结果在荷兰的志愿者队列中也得到了验证。
Raes教授在肠道微生物领域是很有名气的,他在2011年的时候率先提出了“肠型(enterotype)”的概念[4],因为即使同为健康人群,大家的肠道微生物组成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的,肠型就是根据肠道中占主导地位的优势菌种类进行划分,传统分法包括3种:拟杆菌型(Bacteroides)、普氏菌型(Prevotella)和瘤胃球菌型(Ruminococcus)。
在2017年的时候,Raes教授再次取得突破,他发现拟杆菌型肠型中有一小部分与大多数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于是他将拟杆菌型拆分成了1型和2型[5]。2型拟杆菌型肠型的特点是是总体微生物载量很低,而且,这是最接近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的一种)患者肠道菌群组成的一种肠型。这次Raes教授又发现,2型拟杆菌型肠型和抑郁症还有低生活质量也有关联!这也是首次将肠型与心理健康状态联系起来。
为了研究肠道微生物与大脑之间,除了分类学之外的联系,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一个模块分析框架,可以描述微生物途径(代谢化合物)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联。他们从综合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中调取了532个人胃肠道中微生物的基因组,这些微生物能够产生一些神经活性物质,影响神经功能,研究人员将它们整合成了第一个肠道微生物神经活性物质目录。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就像研究的第一作者Mireia Valles-Colomer博士说的,许多神经活性物质是在肠道中产生的,比如多巴胺,这个分析工具可以帮助识别哪些肠道微生物参与产生、修饰或是降解这些物质,进一步还可以识别影响心理健康状况的微生物以及可能涉及的机制[6]。
为了展示一下这个工具的“本事”,在这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他们发现,微生物产生DOPAC(3,4-二羟基苯乙酸,多巴胺经单胺氧化酶降解后的产物)的能力越强,生活质量越高。根据过去的研究,DOPAC能够抑制结肠癌细胞的增殖[7],而且它的水平的下降也是帕金森病的一个标志[8],这两点也反面映衬了研究人员的分析结果。当然,分析结果是生物信息学的产物,未来,还需要实验来证实。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给“肠道微生物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关联”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更高的生活质量可能与高丰度的粪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细菌有关,而抑郁症则可能与小杆菌属和粪球菌属细菌减少有关。
不过,肠道微生物在抑郁症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是不确定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meran Mayer教授表示,这个研究使我们对肠道与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认识更近了一步,但是从治疗的角度上来说,她认为单独地补充某些益生菌可能并不能解决问题,毕竟微生物组和抑郁症都很复杂,只有“全局性”的改善微生物平衡或许才是最好的办法[9]。
参考资料:
[1] The neuroactive potential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in quality of life and depression[J]. Nature Microbiology, 2019: 1.
[2] The treatment-naive microbiome in new-onset Crohn’s disease[J]. Cell host & microbe, 2014, 15(3): 382-392.
[3] Altered fecal microbiota composition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015, 48: 186-194.
[4] Enterotypes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J].nature, 2011, 473(7346): 174-180.
[5] Quantitative microbiome profiling links gutcommunity variation to microbial load[J]. Nature, 2017, 551(7681): 507.
[6]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9/02/190204114617.htm
[7] Of the major phenolic acids formed during human microbial fermentation of tea, citrus, and soy flavonoid supplements, only 3, 4-dihydroxyphenylacetic acid has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J].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2006, 136(1): 52-57.
[8] Cerebrospinal fluid biomarkers of central dopamine deficiency predict Parkinson's disease[J]. Parkinsonism & related disorders, 2018, 50: 108-112.
[9] https://phys.org/news/2019-02-germs-gut-depression.html
标签: 肠道菌群